阿伯特:芝加哥大學(xué)與社會學(xué)研究
日期:2020年11月01日
正文共:9813字5圖
預(yù)計閱讀時間:25分鐘
來源:新浪科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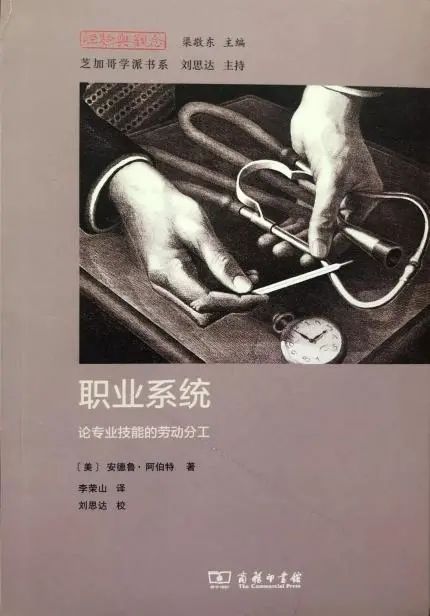
—?THE END —

評論
圖片
表情
<b id="afajh"><abbr id="afajh"></abbr></b>
 下載APP
下載APP日期:2020年11月01日
正文共:9813字5圖
預(yù)計閱讀時間:25分鐘
來源:新浪科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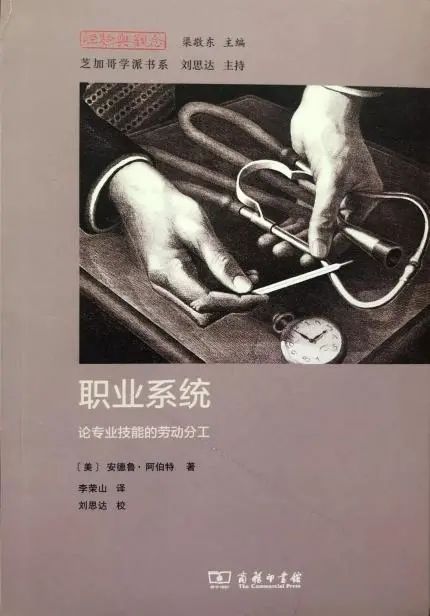
—?THE END —

<b id="afajh"><abbr id="afajh"></abbr></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