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戲的特質(zhì):當(dāng)我們說“play”的時候,究竟在說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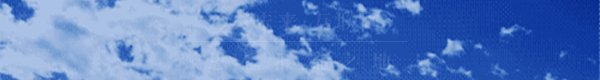

在中文語境中,說起“玩”,我們常常會產(chǎn)生“把玩”等聯(lián)想;而在英文中,說到“play”時,又常常意味著比賽或演奏樂器。這些含義都與我們當(dāng)下所說的“玩游戲”相去甚遠(yuǎn)。正因如此,隨著游戲形態(tài)的不斷演變,我們也需要重新審視“play”的含義。

從20世紀(jì)后半葉開始,新媒體技術(shù)蓬勃發(fā)展,同時期發(fā)展的新媒介理論也開始重新討論諸如數(shù)字信息時代電影或者戲劇等傳統(tǒng)藝術(shù)。然而,伴隨著20世紀(jì)電子計算機技術(shù)的誕生,同時產(chǎn)生了一種新的媒體通過數(shù)位編碼和顯像技術(shù),這就是電子游戲。
電子游戲的媒介歷史可以追溯到電子計算機技術(shù)誕生之初,然而當(dāng)我們使用“電子游戲”這個中文詞匯討論這些媒體時,我們翻譯并引用的英文原詞應(yīng)該是“Electronic Game”還是“Video Game”?
其實早在計算機還在開發(fā)的20世紀(jì)30年代,荷蘭學(xué)者赫伊津哈已經(jīng)展開了一系列關(guān)于游戲的研究,而“游戲”與“玩”之間的關(guān)系是如何辨析的,赫伊津哈的著作《游戲的人》 已經(jīng)進行了詳細(xì)的論述。
赫伊津哈總結(jié)出了游戲活動的三大特征:
游戲是自由的。游戲是非物質(zhì)、非理性的行為,不帶有任何功利目的。它遵循自由參加的原則,受命參與的游戲就不再是游戲,最多只能算對游戲行為的模仿。
游戲有別于真實生活。游戲是暫時創(chuàng)造出一片完全由游戲規(guī)則支配的空間,每個參與游戲的人都心知肚明他們“只是在假裝”,或者說只是好玩而已。
游戲受限制。限制游戲進行的條件很多,比如必需有進行游戲的空間、游戲規(guī)則、需要在特定時刻終止等等。但因為游戲受限制、有自己的進程,決定了它是可重復(fù)的,能夠形成文化和傳統(tǒng)。幾乎所有游戲都有重復(fù)或交替要素。
在此基礎(chǔ)上,赫伊津哈給“游戲”這一概念下了明確的定義:
游戲是在特定時空范圍內(nèi)進行的一種自愿活動或消遣;遵循自愿接受但又有絕對約束力的原則,以自身為目的,伴隨有緊張感、喜悅感,并意識到它不同于平常生活。
基于此定義,赫伊津哈開始據(jù)此分析游戲與文化的關(guān)系。而我們也可以對中文語言現(xiàn)象中的“游戲”與“玩”的具體用法進行研究。
在中文翻譯為“玩”以及“玩家”的概念,其詞源不是拉丁語的Ludus。中國傳統(tǒng)意義的“玩”與“把玩”玉器有關(guān),這里所指與我們要討論的新媒體理論相距甚遠(yuǎn),我們不展開討論。
另一方面,在大量國內(nèi)的新媒介理論中,對于“電子游戲”和“電子游戲玩家”的使用基本都是在借用“Play”這個詞匯,以及其在英語中所指的范疇。可這一用法導(dǎo)致的問題恰恰在于,因為英語中“Play”與“Player”這個概念囊括的領(lǐng)域比拉丁語Ludere還廣,所以“Play”的專門含義完全被“輕松的活動”和“運動”的含義掩蓋(在日耳曼語族中顯得更為明顯)。
我們無法就“Play”所有能指的起源進行密集排查工作,而且現(xiàn)代漢語書寫的媒介理論中“玩家”的概念雖然直接翻譯來自英文“Player”,但具體到語境中使用也有很大的出入(比如Player也指競賽運動員、樂器演奏家,但中文的“玩家”并沒有對應(yīng)的含義)。
所以,基于這樣的背景,我們有必要就“電子游戲”中“游戲活動”概念的使用環(huán)境展開具體的討論。
01
對比:傳統(tǒng)游戲與電子游戲

路德維希·維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是第一位提對“Play”一詞定義的分析哲學(xué)家。在維特根斯坦的哲學(xué)研究中,他認(rèn)為游戲的要素,如游戲活動、游戲規(guī)則和游戲中的競爭,都不能充分定義游戲是什么。
維特根斯坦由此得出結(jié)論,人們將“游戲”一詞應(yīng)用于一系列不同的人類活動,而這些活動彼此之間只具有人們可能稱之為家族相似性的東西。
家族相似性(德語:Familien?hnlichkeit),即用同一個字代表不同的事物或者狀態(tài)。這些事物或者狀態(tài),雖然彼此之間不同,卻如家族成員般從屬于同一家庭,而具備某些相似的特征。例如,在日常生活的語言里,“游戲”一詞可指稱各種活動,如下棋、打棒球、“人生是一場game”等。但這些活動卻無相同的特質(zhì),只有家族相似性而已。正如一家之中,兄弟姐妹,個個長得相似,但他們并不因此就不從屬在同一個家庭。
以下是我們可以找到在一系列當(dāng)今社常見的游戲活動,它們都以“Game”為共有名稱,以“Play”統(tǒng)一命名在此類活動中的行為。
那么電子游戲又有哪些特征與傳統(tǒng)游戲相似呢?我們再來進行類型列舉分析:
以上多類游戲活動中play所指代的具體行為命名,我們會發(fā)現(xiàn),確實如維特根斯坦所說,游戲之間存在著大量的家族相似,所以只能用play來籠統(tǒng)地進行命名。但是這些游戲之間又并非沒有一個共同的特征。
但游戲形式和具體游戲的規(guī)則是瞬息萬變的,維特根斯坦時代所需要面對和處理的游戲定義問題其實并沒有今天這樣復(fù)雜——新媒體崛起之后,大量的傳統(tǒng)游戲活動被以編碼的形式重新模擬編寫稱為具體的游戲軟件,這才是游戲和玩家更需要被重新認(rèn)識的原因。
雖然“家族相似”的提出,將游戲的“本體論”問題引向了一個通過認(rèn)識游戲并為其命名的語言學(xué)問題,避免了方法論爭執(zhí)的必要,但這些看似共同特征和所謂內(nèi)在規(guī)律,其實是人類因為自身描述的需要從現(xiàn)象中抽象出來的。這種從特殊現(xiàn)象到一般符號的思維方式是所有語言游戲的基礎(chǔ)。
所以,當(dāng)我們建立對游戲和玩家命名的分析時,需要回到具體的游戲活動想象中去進行把握。
我們將“Play”這一詞匯的能指所對應(yīng)的“游戲活動”進行映射,我們可以看到它作為一個動詞,它標(biāo)記的是一種人類活動。那么至少從這個角度講,“play”是具有本質(zhì)的,它的本質(zhì)就是一種“人類活動”。
如Roger Caillois在其著作“Man, play, and games”所言:
“總結(jié)游戲的形式特征,我們可以把它稱為一種自覺地站在‘平凡’生活之外的‘不嚴(yán)肅’的自由活動,同時又強烈而徹底地吸引著玩家。”
到這里,通過本節(jié)內(nèi)容中所討論的傳統(tǒng)游戲活動與電子游戲活動進行家族相似對比,我們會發(fā)現(xiàn),電子游戲其實遠(yuǎn)比傳統(tǒng)的游戲活動中所出現(xiàn)的形式都復(fù)雜很多。它對社會,對審美,甚至對意識形態(tài)都產(chǎn)生了不同側(cè)面的影響。
那么要討論游戲的社會意義,必然要先從游戲活動中玩家的行為模式去分析。
02
樂趣是游戲的核心要素

游戲不是人類獨有的現(xiàn)象。我們通過觀察小動物發(fā)現(xiàn),動物天生就會玩游戲,不需要任何教育。并且人類游戲的一切基本要素,都體現(xiàn)在小貓小狗歡快的嬉鬧中了——盡管人類的游戲規(guī)則更復(fù)雜、形式更先進,但從形式創(chuàng)新上說,人類并未給“游戲”這一概念賦予任何人類獨有特征。
游戲似乎是一種生物本能,但用“本能”或者“天生”解釋這個問題未免流于粗淺。長久以來,生物學(xué)和心理學(xué)研究嘗試給游戲賦予各種各樣的意義,最有市場的理論是行為心理學(xué)家們在20世紀(jì)初所進行的嘗試——“通過游戲?qū)τ啄晟镏橇蛭锢砩系哪承C理進行鍛煉”,以適應(yīng)未來嚴(yán)酷的生存環(huán)境。其他研究成果還包括“釋放過剩精力、放松身心、補償落空期待、生物發(fā)泄某種先天才能的沖動”等等 。
赫伊津哈認(rèn)為,以上說法都在邏輯上犯了同一個錯誤,即先入為主地斷定游戲必定在為某種不是游戲的東西服務(wù),具有生物學(xué)或功利的目的。這些理論完全忽視了游戲的“樂趣”,而樂趣恰恰才是游戲活動的核心要素。
游戲活動通過追求自由而獲得的愉悅與樂趣,會導(dǎo)致以上結(jié)論蒼白無力——如果具有目的的所有生命活動都可以通過機械鍛煉實現(xiàn),為什么自然選擇和進化賦予我們游戲的能力?難道游戲只是一個沒有具體所指的符號么?事實上,游戲行為遠(yuǎn)超出了人類生活的領(lǐng)域,也就不以任何約定或者被規(guī)訓(xùn)的理性關(guān)系為基礎(chǔ),如若不然,游戲現(xiàn)象便該限于人類專有了。
當(dāng)代電子游戲的研究者和學(xué)者,窮究心智與時間,力圖向世人證明游戲或者電子游戲有豐富的社會和文化價值,這是一個值得尊敬的行業(yè)——但卻被精通古代歷史文獻的先賢呵斥:“游戲并不追求有用,而是追自由!”
值得慶幸的是,赫伊津哈除了棒喝,還遞給我們啟發(fā)的火種:人的價值觀不應(yīng)該只圍繞“有用”這一個維度來討論。我們在物質(zhì)之上構(gòu)筑精神世界,而對游戲的思考也應(yīng)該延展到那個領(lǐng)域:
“承認(rèn)了游戲的存在,也就承認(rèn)了精神的存在,因為不論游戲是什么,它都不會是物質(zhì)。即便在動物界,游戲也掙脫了物質(zhì)的束縛。如果認(rèn)為世界完全受盲目力量支配的話,游戲就純屬多余了——
只有精神的洪流沖垮了為所欲為的宇宙決定論,游戲才有可能存在……人類社會超越邏輯推理的天性才能不斷被證實。動物會玩游戲,因此它們不只是單純的機械物體;我們會玩游戲,而且知道自己在玩游戲,因此我們必定不只是單純的理性生物,因為游戲是無理性的。”
結(jié)合和赫伊津哈和維特根斯坦的觀點,我們可以看出,至少游戲(game)是指人類的特殊活動,我們統(tǒng)稱它為“play”。游戲活動是一類沒有具體概念可以直接把握的人類活動,這些活動遵循著某種規(guī)則,規(guī)則之間具有家族相似的特征。
根據(jù)以上的分析,“play”作為某種具有家族特征的行為活動,不但提供了特征,而且提供了“本質(zhì)”,特征和本質(zhì)結(jié)合起來就構(gòu)成了游戲家族的“特質(zhì)”。具體說來,游戲特質(zhì)就是這個集合中所有家族成員特征所依賴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的特性。游戲構(gòu)成一個家族,其成員不僅是相似的問題,而且有一個共同的內(nèi)在結(jié)構(gòu),即游戲的內(nèi)在機制(比如說,要由一個或多個人進行操作活動)。
這種機制在游戲存在的每一個可能形式中是同樣的,并且現(xiàn)實世界的傳統(tǒng)游戲與數(shù)碼世界的電子游戲,如果它們有相同的機制,那么它們就是同樣的游戲。家族相似的分析法背后對游戲的內(nèi)部結(jié)構(gòu)是持肯定態(tài)度的,比如“家族遺傳密碼”的結(jié)構(gòu)。不管怎么說,一個家族總有它的遺傳密碼結(jié)構(gòu),并且如果在現(xiàn)象世界中的家族與編碼世界或者語言世界中的家族有相同的遺傳密碼結(jié)構(gòu),那么它們就是同一個家族。
赫伊津哈論證,藝術(shù)是從游戲中誕生,并作為游戲發(fā)展起來的。然而游戲本身要發(fā)展成藝術(shù),要面對其他藝術(shù)門類都沒有的邏輯悖論:它還是游戲嗎?各種藝術(shù)門類一旦發(fā)展成熟,即便它們在機制上還保有游戲元素,但也不再是游戲了——好比戲劇,在原始階段就是游戲,待其發(fā)展成熟,被定性為“藝術(shù)”后便脫離了“游戲”范疇,但它仍是戲劇——保留了自己作為戲劇被規(guī)定那個的本質(zhì)屬性。
電子游戲不一定必要被歸為“第九藝術(shù)” ,但不可否認(rèn)的是,電子游戲是人類廣泛的游戲活動(play)中產(chǎn)生的游戲家族(Family of Games)中的一員。它和其他傳統(tǒng)游戲有著親緣關(guān)系,而部分藝術(shù)如戲劇,音樂包括詩歌等也同樣產(chǎn)出自古代人類的游戲活動,親緣沒有是非只有遠(yuǎn)近。
如果把電子游戲放入藝術(shù)的范疇中討論,那么它還需要接受藝術(shù)體制的規(guī)訓(xùn),而這對于電子游戲是一種二次桎梏。因為電子游戲本來就是以追求自由而進行的游戲活動中被拋下變成具體規(guī)則的游戲產(chǎn)品,再從對它進行第二次規(guī)范著實相比其初衷早已背道而馳。
03
總結(jié)

通過細(xì)分游戲活動中玩家不同的行為,以及豐富的精神活動狀態(tài),我們會發(fā)現(xiàn),傳統(tǒng)媒介理論只通過媒介劃分來討論“電子游戲”和“電子游戲玩家”的方法會產(chǎn)生大量的概念混淆。
傳統(tǒng)媒介理論對玩家和游戲的理解,無法有效識別“電子游戲玩家”與“電子游戲職業(yè)勞動者”,更重要的是無法與那些認(rèn)同“電子游戲成癮論”的人群開展有信息交換的正確對話,致使大量的數(shù)據(jù)統(tǒng)計研究以及對電子游戲的社會管理失效。
“玩游戲”或許是一種在反復(fù)訓(xùn)練同時還需要隨時帶入反思狀態(tài)的人類活動。我們仔細(xì)研究赫伊津哈對游戲的定義會發(fā)現(xiàn),游戲的定義其實不只界定了“游戲”的性質(zhì),對人的“游戲狀態(tài)”也是有要求的,大抵包括參與自由、非功利、能隨時終止等等。對于所謂的沉迷者,無法區(qū)分“游戲”與“現(xiàn)實”,無法靠自己的意志選擇適時地結(jié)束這種活動,這種狀態(tài)其實是很不具有“游戲精神”的游戲行為。
很多時候人們并不是想“玩游戲”,只是現(xiàn)代勞動-空閑的生活節(jié)奏中,人們經(jīng)常只想無意義地度過一段時間。按赫伊津哈理論,當(dāng)我們處于這種狀態(tài)下,也不能定性為“游戲”,因為我們某種程度上是“別無選擇”并非純粹自由參與了游戲活動的,且?guī)в型ㄟ^“游戲”打發(fā)時間的功利性。同時,這或許能解釋為什么當(dāng)我們在這種狀態(tài)下玩游戲,往往無法體會到多少樂趣。
電子游戲作為模擬傳統(tǒng)游戲活動的數(shù)位編碼軟件,它本身具有媒介理論所描述的特征,但電子游戲玩家作為人類,他們所進行的游戲活動,需要從傳統(tǒng)游戲活動的理論中去找描述方法。
當(dāng)我們清楚分辨了“play”與“game”的不同所指,我們才能識別游戲活動的特質(zhì),并理解赫伊津哈站在傳統(tǒng)游戲理論對20世紀(jì)后人類游戲行為的批判與反思——如何在規(guī)則的枷鎖中追求自由的超越。![]()
--------------- 往期回顧 ---------------
點擊文末“閱讀原文”,查看更多關(guān)于電子游戲的討論



